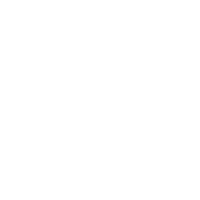(本文2014年6月12日发布于凤凰网//news.ifeng.com/opinion/wangping/xianggangjibenfa/index.shtm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白皮书的第五部分“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无疑是整个文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香港当前和将来可能面对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基础。在本部分,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
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指出了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法理依据。过去一段时间内,香港社会存在一些对特区法治基础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香港人民有权进行公投决定香港特区政制发展路径、香港是“次主权实体”、中央除国防和外交外不对香港行使其他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干涉香港司法独立等,均与对香港法治基础的认识有关,即认为基本法排除了宪法在香港的效力、宪法因而不再在香港特区实施。针对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白皮书明确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这有助于廓清香港法治的正当性依据,明确宪法在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
更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基础并非意味着在特区宪法与基本法的地位平行、作用等量。恰恰相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全国范围包括香港特区有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是位居宪法之下的全国性法律。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基本法不得排斥宪法在特区的适用,这是理解香港法治问题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宪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作为授权法的香港基本法其正当性依据只能从宪法中获取。
主权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诞生的概念,出现于16世纪后半叶。最早论述主权的法国思想博丹在《国家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中指出,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作为近现代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无疑是承载和体现主权的最好法律。宪法代表国家主权,主权只能由全国人民行使,而宪法恰是全国人民政治决断的产物,所以其有权决定整个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包括采取何种类型的地方制度。
主权问题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香港的主权从来属于中国。1984年12月2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我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一句匠心独运而又寓意深刻的表述,其寓意在于:自古以来,中国对香港就拥有主权,只是碍于一些原因,在一段时间内没能行使主权,也就是此时期内,香港的主权和体现主权的治权暂时分离了,但自1997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主权和治权的统一。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就意味着体现国家主权的宪法开始在香港实施。
虽然宪法在香港实施,但1982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时,“一国两制”的思想提出不久,其系统性还不充足、内容还未定型,所以无法在宪法中对香港澳门未来的治理方式作出详细规定,而只是在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并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规定在特区实行的制度,而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在1990年根据宪法而制定的。所以,宪法是全国人民政治决断的产物,而香港基本法不是香港居民政治决断的产物,而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地位不可与宪法齐观。按照2012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来看,基本法隶属于我国的宪法相关法,而宪法是凌驾于包括宪法相关法在内的七大部门法之上的国家根本法。
强调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意味着基本法无法排斥宪法在特区的效力。虽然基本法第11条规定,在特区实行的一切制度均以基本法为依据,但这并不表明基本法成为特区的最高法。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否认宪法在特区的效力,将使基本法丧失合法性依据。因为前文已经指出,香港并不享有主权,其居民不享有通过制定宪法决定自己政治治理结构的政治决断权,所以基本法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其效力在宪法之下。下位法不能决定上位法的效力,也不能排斥其适用乃是法理学上的基本规则。如果宪法不在特区实施将使基本法变成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基本法在香港的宪制性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强调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还意味着特区权力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基本法规定的,而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所以在逻辑上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并非来源于英国人撤走时的遗留,而是英国人在撤走时将治理香港的权力作为主权的重要内容归还于我国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再根据宪法制定基本法授予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本法是一部中央向特区的授权法,而不是香港居民向特区政府的授权法。从授权法的角度而言,被授权者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能超越授权的范围;而授权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授权的内容。所以,基本法并非是联邦制国家宪法那样的分权法,在基本法理论中也不存在如联邦制国家那样分而未尽的“剩余权力”。
强调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还意味着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的权力不仅来源于基本法,也来源于宪法。宪法对中央政府权力的规定只要不违反“一国两制”的原则,均可以对特区政府行使。不能抽象对将宪法规定的中央政府各项权力与基本法规定的中央对特区行使的各项权力割裂开来。事实上,基本法当中的有关中央对特区行使的诸多权力恰恰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如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决定紧急状态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对应的一般性规定,只不过基本法将其具体化了而已。这也是白皮书提出的中央拥有对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法律依据所在。(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